文 / 鄭春鴻
這些年來,我有一個習慣,只要看到乞丐,完全不假思索,就會把手伸進口袋,掏出幾個銅板給他。像這樣的直覺動作,在更年輕的時候,我並不是這麼做的。
過去,我也會給行乞者錢,但每一次它都是選擇性地、獨立的事件,因為在施捨之前,我通常會打量一下,看看這個衣衫襤褸的人是真的?還是裝的?
我不喜歡不像乞丐的乞丐,比如有一些乞丐打扮得實在很不怎麼高明,他身上衣服的百衲補丁,補得實在太整齊了,顏色太多了,太像道具了;有的人的腿打了一個石膏,有兩條腿那麼粗,我想像不出有哪一個拙劣的醫師會把病人的傷口包裹成這付德性;我也不喜歡故意悲情的乞丐,比如在傳統市場看到打赤膊全身趴在地上,一邊爬,一邊還有配樂,雖然他是肢體殘障,但是總叫人感到太矯情、太表演了,令人見了感到就算給他再多的錢,好像也沒幫上他的忙。我更不喜歡太職業的乞丐,比如某一位乞者每天固定在一處,對每一位經過的人都問好:「您好!祝您身體健康」,到了星期五,還會改口:「祝您周末愉快」。這樣多禮等於每天都在提醒大家要注意他,讓人似乎沒有拒絕的權利。
即使我對上列諸丐有這樣苛刻的挑剔,但是他們並沒有要求你給多少錢,每次你都可以隨便往口袋裡掏,十元、廿元、五十元隨意給;另一種也可以歸為丐幫,但算是求援者,門檻就稍高,台灣從南到北,幾乎都是一口價,要一百元起跳。
他們通常是兩人組,專門在夜市逐攤逐桌推銷日用品,一位坐在輪椅,一位是推手,一包市售不到五十元的抹布、幾支簽字筆就要價一百元。有時候我們到夜市吃碗麵,也花不了五十元,一下子要你樂捐一百元,而且不能更少,實在有點強人所難。只有在一桌人在吃飯時,這樣的推銷成交的機會就比較大。大伙兒大魚大肉,身邊突然出現一對不幸的夫婦求援,飯局的東家為了維持餐桌的氣氛,也為了表現自己並不冷血,通常嘖有煩言不耐地掏出一百元,隨便挑一樣東西打發走人。
至於從什麼時候開始,我就不再打量乞丐的外表和行為,只要看到乞者一定給錢呢?
我想大概是在兩年前,我每天上班經過台北火車站捷運的某一入口,總看到一位年紀很大的阿嬤,她在樓梯角落蜷縮著嶙峋的身子,不喃喃自語,也不對施捨者稱謝,只有等著。這個阿嬤頭上包著一條黑色的頭巾,她穿的上衣和褲子不論樣式或顏色是那麼不搭配,一看就知道是別人分別送她的。不過她不像其他遊民髒兮兮的,而總是素素淨淨的,保持一個老人家應有的基本尊嚴,完全吻合我心目中典型乞者的形象。我每天一定給她夠吃早餐的錢,本來她都不抬頭的,但是日子久了,我發現一接近她,她會仰起很小角的度露出塌陷的眼瞼看我一眼,並且給我一個應該算微笑,不過它的強度大約只有一般人所謂的微笑的千分之一吧!極弱的笑意,它像綻開之前裹在花瓣裡含苞的一笑,從眸中流洩出來,比較接近一絲意念,一個善意的回應。
就這樣,那一陣子我好像把老阿嬤的早餐當做我的責任,不過也不盡然,因為我並沒有特別去理會她在我休假不上班的日子,到底有沒有錢吃早飯。一直到有一天,我發現老阿嬤不見了,而且連著幾天都不見了,本來我不太以為意,但是慢慢有點擔心她會不會病了,去看醫生了嗎?她會不會過世了?每天上班走到那個角落,好像有一種少做了什麼應該做的事的感覺。
這樣又過幾個月後的某一天,我在同一個角落才又看到老阿嬤,當我靠近她,與她悄悄地望著我的時候,我突然發現,在老阿嬤不見的這段日子,我失去的,我想要找尋的,正是那她小仰角對我注視時發出的那千分之一強度的微笑。
我忽然想起馬太福音的一句話:「我實在告訴你們,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,就是作在我身上了。」是我施捨給老阿嬤嗎?她好像給我的更多一些。我輕易給出三、五十元,就想支配一個老人給我一次苦境的表演嗎?事實上,我給行乞者一些錢,幫上他們的可能不多,反倒是填補自己、滿足自己因施捨而獲取的快意和滿足或許更多一些吧!倘此為真,我又有什麼資格在丟給人家幾塊錢之前,給他做什麼身家調查呢?
這些年來,我有一個習慣,只要看到乞丐,完全不假思索,就會把手伸進口袋,掏出幾個銅板給他。像這樣的直覺動作,在更年輕的時候,我並不是這麼做的。
過去,我也會給行乞者錢,但每一次它都是選擇性地、獨立的事件,因為在施捨之前,我通常會打量一下,看看這個衣衫襤褸的人是真的?還是裝的?
我不喜歡不像乞丐的乞丐,比如有一些乞丐打扮得實在很不怎麼高明,他身上衣服的百衲補丁,補得實在太整齊了,顏色太多了,太像道具了;有的人的腿打了一個石膏,有兩條腿那麼粗,我想像不出有哪一個拙劣的醫師會把病人的傷口包裹成這付德性;我也不喜歡故意悲情的乞丐,比如在傳統市場看到打赤膊全身趴在地上,一邊爬,一邊還有配樂,雖然他是肢體殘障,但是總叫人感到太矯情、太表演了,令人見了感到就算給他再多的錢,好像也沒幫上他的忙。我更不喜歡太職業的乞丐,比如某一位乞者每天固定在一處,對每一位經過的人都問好:「您好!祝您身體健康」,到了星期五,還會改口:「祝您周末愉快」。這樣多禮等於每天都在提醒大家要注意他,讓人似乎沒有拒絕的權利。
即使我對上列諸丐有這樣苛刻的挑剔,但是他們並沒有要求你給多少錢,每次你都可以隨便往口袋裡掏,十元、廿元、五十元隨意給;另一種也可以歸為丐幫,但算是求援者,門檻就稍高,台灣從南到北,幾乎都是一口價,要一百元起跳。
他們通常是兩人組,專門在夜市逐攤逐桌推銷日用品,一位坐在輪椅,一位是推手,一包市售不到五十元的抹布、幾支簽字筆就要價一百元。有時候我們到夜市吃碗麵,也花不了五十元,一下子要你樂捐一百元,而且不能更少,實在有點強人所難。只有在一桌人在吃飯時,這樣的推銷成交的機會就比較大。大伙兒大魚大肉,身邊突然出現一對不幸的夫婦求援,飯局的東家為了維持餐桌的氣氛,也為了表現自己並不冷血,通常嘖有煩言不耐地掏出一百元,隨便挑一樣東西打發走人。
至於從什麼時候開始,我就不再打量乞丐的外表和行為,只要看到乞者一定給錢呢?
我想大概是在兩年前,我每天上班經過台北火車站捷運的某一入口,總看到一位年紀很大的阿嬤,她在樓梯角落蜷縮著嶙峋的身子,不喃喃自語,也不對施捨者稱謝,只有等著。這個阿嬤頭上包著一條黑色的頭巾,她穿的上衣和褲子不論樣式或顏色是那麼不搭配,一看就知道是別人分別送她的。不過她不像其他遊民髒兮兮的,而總是素素淨淨的,保持一個老人家應有的基本尊嚴,完全吻合我心目中典型乞者的形象。我每天一定給她夠吃早餐的錢,本來她都不抬頭的,但是日子久了,我發現一接近她,她會仰起很小角的度露出塌陷的眼瞼看我一眼,並且給我一個應該算微笑,不過它的強度大約只有一般人所謂的微笑的千分之一吧!極弱的笑意,它像綻開之前裹在花瓣裡含苞的一笑,從眸中流洩出來,比較接近一絲意念,一個善意的回應。
就這樣,那一陣子我好像把老阿嬤的早餐當做我的責任,不過也不盡然,因為我並沒有特別去理會她在我休假不上班的日子,到底有沒有錢吃早飯。一直到有一天,我發現老阿嬤不見了,而且連著幾天都不見了,本來我不太以為意,但是慢慢有點擔心她會不會病了,去看醫生了嗎?她會不會過世了?每天上班走到那個角落,好像有一種少做了什麼應該做的事的感覺。
這樣又過幾個月後的某一天,我在同一個角落才又看到老阿嬤,當我靠近她,與她悄悄地望著我的時候,我突然發現,在老阿嬤不見的這段日子,我失去的,我想要找尋的,正是那她小仰角對我注視時發出的那千分之一強度的微笑。
我忽然想起馬太福音的一句話:「我實在告訴你們,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,就是作在我身上了。」是我施捨給老阿嬤嗎?她好像給我的更多一些。我輕易給出三、五十元,就想支配一個老人給我一次苦境的表演嗎?事實上,我給行乞者一些錢,幫上他們的可能不多,反倒是填補自己、滿足自己因施捨而獲取的快意和滿足或許更多一些吧!倘此為真,我又有什麼資格在丟給人家幾塊錢之前,給他做什麼身家調查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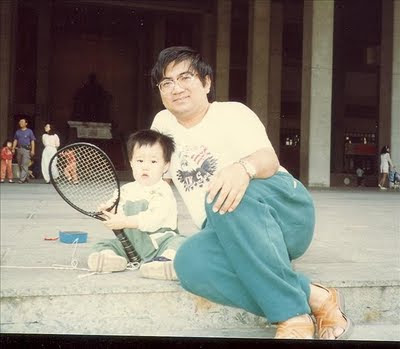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